中式教育和美式教育的差别到底在哪里?
网上有关“中式教育和美式教育的差别到底在哪里?”话题很是火热,小编也是针对中式教育和美式教育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寻找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一些信息进行分析,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现代教育的问题本质上是经济问题。国人往往愿意夸大中国教育的缺点,无视美国教育的问题和现代教育的本质矛盾,而把自己的种种和中国社会发展某些方面的问题归咎于中国的教育上。
1. 适当的应试教育不会摧残人的创造力
人们常常批评中国教育的一点就是认为孩子们天天应试会伤害孩子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展。对此最佳的反例就是韩国。韩国应试教育比中国还要残酷,进行全面的量化管理。然而韩国不仅技术创新做得比中国多,球踢得还比中国好,**拍得比中国强,连肥皂剧和综艺节目做得都比中国专业。这是为什么?
在以上的每一个细分领域讨论中国同韩国差距的原因,都可以另写一篇答案。但一个共同点是,韩国在以上的每个领域都创造了一个健康的人才市场。既然是市场就要符合经济学原理。而一个重要的经济学原理就是:人们会对激励作出反应。具体到人才市场就是,人们会为了得到想要的工作机会而努力获得相应的培训,无论这份工作是科学家,工程师,还是足球运动员。中国学术圈的问题,不是因为应试教育影响了孩子们的创新能力,而是因为认真的科研没有得到足够的激励,对腐败造假的纵容包庇伤害了科研人才的市场。
再说一个例子:IMO, 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每年,IMO都会把各国选拔出来的孩子们关在一起考试做数学题,根据成绩对国家进行排名。因此大多数竞赛强国都会在考试前的几个月开始对自己国家的国家队选手进行培训。而能进入国家队的孩子,在这之前很可能已经经历过若干年的奥赛教育。因而IMO大概是最为极端的应试教育之一。那些在IMO中获奖的孩子们长大后怎么样了?他们的创新能力还在么?
我们可以从菲尔兹奖,这个被成为“数学家的诺贝尔奖”的获奖结果中看出些一二。从1990年开始算起,每届菲尔兹奖获得者中都会有至少一位是IMO获奖者,一共26位获奖者中有13位是曾经的IMO获奖者。这些在数学研究中做出巨大突破的数学家们,曾经也是应试教育的经历者和优胜者。那场应试,伤害到他们什么了?
人们常常低估市场经济对人才培养和选拔的巨大作用,而夸大了应试教育的负面效果。
2. 量化考核是公共教育的未来
首先明确几个概念。教育的概念其实应该分为两部分:家庭教育和公共教育。前者指代父母,后者指代学校。在接下来的这个段落,我们只讨论公共教育,即学校到底应该怎么教。
很多国人总爱说,美国学校有多好多轻松,老师整天带着孩子们玩,搞素质教育,不像国内天天考试。且不说这种放羊式管理造成了美国理科基础教育的全面落后,更重要的是,在美国,公共教育正在全面走向量化,而且教育越发达的地区量化的程度越高。
GreatSchools Ratings,一种在美国常用的用来评价公立学校的分数体系。每个学校得分在0-10之间。在美国的大部分州,分数完全取决于在校学生的标准化考试成绩。家长们根据学校的分数判断学校的教育质量,从而为孩子选择学校和学区。因此,提高学生们的标准化考试成绩,是学校发展的首要目标。这故事的开局是如此的熟悉,以至于国人不难想像到这场量化运动会走向何处。最终,学校的老师们也将以学生的考试成绩被考核。这将重塑教师的人才市场,并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教育质量。
量化考核是教育工业化进程不可逆转的趋势。
美国早年的放羊式“素质教育”就如同田园牧歌的纯手工时代,而量化考核就是工业革命和社会大分工。你可以指责工业化和社会分工造成了人们异化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你不能否认,工业化和社会分工是发展的必然趋势,它注定要更广泛,因为它更有效率。纯粹而优质的手工业依然存在,但它只会以小众的,高价的形式,去满足那些愿意为了特定质感花更多钱的人。在教育市场,那叫做私立学校。
教育的市场化会做出自发的选择。这是为什么讨论衡水中学是否应该存在没什么意义。衡水模式出现在河北而不是北京上海本身就说明了答案:河北的经济水平只能负担起衡水模式的教育成本与质量比。
人们常常低估经济对教育模式的影响,而高估了人为改革的作用。
3. 素质教育不适合公共教育
素质教育是什么?无论你是指古雅典的柏拉图学园式教育,还是指中国古代的私塾式教育,还是当代教育书籍中的“启发式教育”,都绕不过一件事:这种教育是一对一的,个性化的,针对特定学生的。换句话说,学生/老师比例要足够的低才能保证质量。
这决定了素质教育或许在古代可以行得通,但在现代公共教育绝对不行。因为古代的教育都是给有钱家孩子的,是私人的。而现代公共教育是大规模的,低成本的,以保证尽可能多的孩子接受教育,从本质上就与素质教育的现实基础相违背。想在公共领域实践素质教育,就等同于想让每个孩子都有做科学家的能力因而找大学教授来给小学上课。这既不现实,我们也不需要。
所以素质教育应该在哪里实践?在那些能一个老师只配几个学生的地方:博士生院,私立学校,和家里。(对大多数孩子来说,家里是最容易实践素质教育的地方。换句话说,素质教育应该是家长的责任而不是社会的。多数中国的父母,轻视了自己作为孩子第一个老师的责任)
要求中国的公共教育强行实践素质教育,只会让已经实现工业化的中国课堂退回到放羊式管理。而那些本可以因为标准化考试而让大多数孩子获得的教育,也只会出现在有钱人家的家教课上。
4. 美国的问题:素质教育加重了社会阶级固化
假如一个社会过分强调素质教育,并根据“素质”来进行人才选拔,那会怎么样?那就会像现在的美国一样,只有有钱家的孩子才能上常青藤。因为获得“素质教育”最有效的办法是上私立高中,而要上私立高中首先要有一样东西:钱。
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这三所大学,录取率最高的100所高中,只有6所不是私立的。而私立高中的大部分学生都来自私立初中,私立小学... 这意味着,一个普通的美国中产家庭,从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社会的上升通道,从一开始就狭窄无比。
我们甚至可以怀疑,所谓“素质”教育和“素质”选拔,是不是有产阶级们的阴谋,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否则,为什么亚裔学生在常青藤的录取上一直受到歧视,即使他们连“素质教育”的表现都比白人学生优秀得多?
5. 我们要从美国教育学习什么?
当然,我们还是能从美国教育学到不少,特别是如何在量化考核的同时保证学生福利:
5.1 多次考试取最优
高考为人所诟病的一个问题就是“一考定终身”,偶然的发挥失常对学生个人的伤害太大。这件事美国做得比较好。SAT考试可以每个月都重新考,申请大学时提交其中最好的一次成绩就行。实践的难点是要做到每次考试的标准更一致,而不仅仅是对学生成绩做正态化。
5.2 考试标准的多样性给孩子选择和思考的空间。
高考把孩子们用一个模子打造成型,就忽略了个体的差异化发展。然而量化考核不代表非要有唯一的考核标准。
美国的SAT2考试,作为对SAT基础考试的一个重要补充,需要学生选三个科目来考,难度比SAT高。这让学生有更多的空间对自身的兴趣和选择进行思考,而不是一味的题海。在此之上的AP考试,更是要选一门大学的科目来考察大学入门内容,难度比SAT2和高考都要高得多。这样,以后不打算做数理相关工作的孩子可以只考SAT,对数学有兴趣的再考SAT2的数学,大学想学数学的再考AP的数学,特别厉害的考竞赛。这一整套阶梯化个性化的量化考核标准,值得中国学习。
一句话总结:现代教育的问题本质上是经济问题,在理解这个前提下讨论如何改进中国教育才有意义。
从系统的角度观察组织,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彼得?圣吉的学习型组织是组织系统观察的经典著述。以学习型组织理论为基础的第五项修炼提供了建设学习型组织的方法路径,分别从: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团队学习和系统思考的角度,给出了从个体到团队和组织成长的路径。
在彼得之后,与他合著《学习型组织心灵篇》的奥托?夏莫发展出了《U型理论》,从另一个视角,诠释了在当今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下,组织创新发展的U型路径。奥托认为,U是一个社会技术的操作系统,如同Windows软件对于计算机的作用一样,提供了社会创新变革的系统化解决路径。
而一百多年前,人智学的创始人鲁道夫?史代纳先生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角度提出了三元组织的观念,是对组织系统的另一个角度的深刻诠释。史代纳先生认为组织是一个包含政治、经济和文化在内的三元载体。在这个三元载体种,文化代表了自由创造的意志,是创新的源泉;经济代表了组织发展的博爱力量,带动组织良性循环发展;政治代表了平等合作的规则机制,帮助组织和谐平衡运转。组织的三元系统由组织内不同的单元体系来承担,相对独立,同时又相互关联。在三元组织中,没有那个是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的元,而是分工合作,协调运转,在不同的职责范围内展开工作,但如同齿轮相互咬合一样,紧密配合实现系统的循环运转。
在三元组织建设中,三元重合的部分发生根本作用的是“人”,是具有独立自主精神,具有领导力、创造力、身心灵健康协同的完整的人。这与学习型组织注重个体成长与组织协同的五项修炼的基础类似。也与奥托在U的变革路径中,最重要的是个体的觉知,群体一起深度下潜找到问题根源的自然流线的穿越完全一致,都是在组织发展的过程中,找到个体协同一致的力量,然后激发个体的力量,带动集体场域的变化,导向一个自我进化,不断更新和自我完善的组织系统。
巧合的是,奥托先生出生于德国,在华德福学校中长大,自小开始也是在史代纳先生构建的人智学的教学体系下成长。所以我想奥托先生的U的理论,整合了系统动力学的先进成果,同时也蕴含着史代纳先生三元组织的背景思想。
与组织的三元系统对应的是,在人智学的观点中,人也可以通过:思考(Thinking)、情感(Feeling)、意志(Willing)的三元系统来观察。思考由神经和新陈代谢系统来承担;情感通过心脏韵律系统来体现;意志透过四肢和感官系统来表现。这便是结合了人的物质体运转的基本规律的系统观察。
联系人的三元系统和组织三元系统,从一个小的生命体到大的生命系统,通常认为文化与意志相关,是创新的基础;经济与情感相关,是连接的纽带;政治与思考一致,决定运转的规则。
从奥托先生倡导的生态角度来看,人体便是一个可以自循环的生态体系,而从单一个体的人,到组织运转的小社会生态体系,便需要组织内的个体通过观察发现问题的根源,建立起共同愿景,找到共同一致努力的目标和方向。所以,个体三元与组织三元一一对应,也证明了从一个小生态到大生态的良性循环的殊途同归的解决路径。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今天我们生活的年代,有幸整合这些大师们的视角和观点,同时结合我们自身所在的组织实践开展深度的探索。这也是我们所处的转型期中国社会,颠覆式变革的互联网时代对我们提出的挑战和要求。这些思想和方法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现实的路径和切实可行的工具帮助我们建设一个有机的组织。
要站在大师的肩膀上,我们还需要一些指引路径的导师,共同成长的益友。所以我们配合来自德国的亚历山大老师发起了这个“IMO横向领导力大师班”的两年制课程,期望能够通过这个课程,帮助到更多的转型期企业的变革发展,在这个新的时代,通过个体横向领导力的发展建设,帮助组织更好的整合外部资源,激发内部优势,导向通往组织成功个体成就的路径。
明年1月,我们在南山等你,一起来,一起践行有机组织,健康社区的创造之旅!
详细了解课程信息,请点击以下链接:
IMO横向领导力大师班
关于“中式教育和美式教育的差别到底在哪里?”这个话题的介绍,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分享完了,如果对你有所帮助请保持对本站的关注!
相关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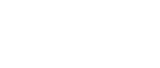
发表评论